阅读是一种名正言顺的贪婪,我们所有的欲望都在阅读中膨胀开来,别想摆脱。思郁便是书痴书狂乃至“书囚”的最好诠释者。他记录下读书过程中的所感所想,不仅仅是对于书的理解,更有对其后生活的解读。起先是读某一个作家,然后按图索骥,晋升到更高级的阅读阶段,进入一个更为澄明的阅读境界。通过“看书人”“写书人”“卖书人”“书之典”铺陈其阅读谱系。这样的阅读示范将把我们带入一个有待填充意义的地带,在混沌的阅读世界中拥有某种神秘的秩序。最终书是生活,书已经是生活,书已经是生活的所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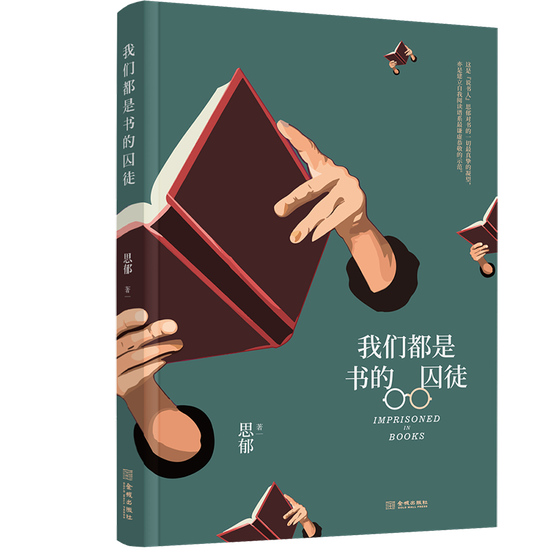
《我们都是书的囚徒》
一本趣味横生又引人深思的“书之书”
关于作家、书店、出版、书中书……
用50余个有关书和阅读的故事
构成一部小巧又集中的书话集
作者简介:
思郁,八十年代生人,书评人、专栏作家。书痴一枚,喜欢阅读,孤独,写作。豆瓣:思郁,微信公众号:书单狗。
编辑推荐:
★这是一本趣味横生又引人深思的“书之书”,豆瓣人气书评人思郁一口气讲了50余个有关书和阅读的故事——关于作家、书店、出版、书中书,构成一部小巧又集中的书话集。这也是一个爱书成痴的人的自白,抽丝剥茧中,我们能发现书和阅读塑造的自己,被书改变的命运,而我们甘愿成为书的囚徒。
★我们处于一个混沌的时代,阅读的指引能让它变得更清晰。思郁以自己广博、循序渐进的阅读为线索,给予读者建立自我阅读谱系最真诚的示范,带你游弋于与书有关的旅程。值得每一个愿意走进阅读的世界,并且愿意长久与阅读为伴的人学习。
★这不是一本方法论,而是对博尔赫斯阅读观的深刻实践。我们谈论博尔赫斯,就必须像博尔赫斯那样去阅读,这也是思郁在阅读旅程中一以贯之的宗旨。我们为什么读经典,怎么聊书背后的故事,从书的阅读而拓展出的人生,看完本书,相信你也会有自己的答案。

序言:书是生活
我对书的最早记忆与阅读的愉悦无关。小时候生活在农村,开始识字后,阅读的欲望乍然膨胀开来,疯狂找寻身边一切关于故事的书籍。那时的农村并没有所谓的文化生活,文学正典更是无迹可寻,所能找到的尽是一些武侠小说之类。印象中最深的一次,夏天的傍晚,家人吃过饭都去串门,我悄悄跑到读高中的姐姐房里找她的书。恰逢父亲回家看到房间的灯亮着,就问了一声。我现在还搞不懂当时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—— 或许是怕被父亲骂看闲 书不好好学习吧,竟然鬼使神差地拉灭了房间的灯,钻到了床底。父亲警觉起来,以为家里进了贼,拿了把扫帚,贴身进门,开灯,扫视,俯身,掀开床帘……
我总觉得有种在阅读与写作的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境遇挥之不去,一如当年我趴在床底接触到父亲眼神那一刹那的尴尬。 这种阅读的焦虑始于一种少年时苦于无书可读的困窘,所以多年后,我读到王小波在《思维的乐趣》中表述的那种下乡时的精神苦闷--“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”--让我仿佛找到了精神上的同类:“傍晚时分,你坐在屋檐下,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,心里寂寞而凄凉,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。”这种切身的精神痛苦,至今弥漫在身,让我惶恐不安。王小波在我早年的阅读谱系上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,不仅仅是因为他对知识的追求让我们体验到一种纯粹智慧 的乐趣,更重要的还有通过王小波,我知道了博尔赫斯,知道了卡尔维诺,知道了罗素,也知道了哲学的智慧。 罗素有很多名言警句,但流传和影响最广的应该是《罗素自传》序言中写到的:“支撑我人生前进的三大动力是对知识的渴求、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人 类苦难不可遏制的怜悯。”罗素的名言中有关于阅读的:“一本书就 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”我的理解就是,他提醒我们写作时要遵循某种阅读与写作的伦理,学着对自己的书写负责。
也许在以后的人生中我们会读很多的书,就像当年我没有书读 的时候会焦虑不安,现在当一本本书越来越多被束之高阁的时候,同样的焦虑不安依然伴随我身。但是,尽管我不停地买书,淘书,书越来越多,但是反而愈发想念年少时读过的那些书。我总是很奇怪,少年时读过那么多的烂书,有些书不但烂,简直烂成了极品,烂到了奇葩的境地,我竟然没有误入歧途,反而由“邪典”堂 而皇之步入“正典”殿堂,这该是多小的概率啊。近读诺奖得主帕慕克的妙文《我如何处理掉我的一些书》,他在其中提到,在处理掉他年少时的一些书时,内心中会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,而之所以感到羞耻,并非因为心里总是不安地想着书房里竟然会有这样一本烂书,而是因为他知道曾经对这本书过分珍视,以至于花钱购买,还让它在书架上端坐多年,“我并非以这本书本身为耻,而是为自己曾如此重视它而感到羞耻”。也许我们都会经过一个口不择食的阅读阶段,一旦当我们拥有了更加清晰而明了的判断力之后,回首旧事,我们的羞耻感就会油然而生。说白了,这也是一种“影响的焦虑”。我们读过某个作家,然后按图索骥,晋升到了更高级的阅读阶段,进入了一个更为澄明的阅读境界,阅读的熏陶 让我们成为一个贪得无厌的读者。 我们所有的欲望只有在阅读中才能光明正大地伸展和膨胀开来,阅读是一种名正言顺的贪婪,喜新厌旧是阅读的合法性诉求。
我很喜欢帕慕克的一个说法:我们重新想起读过的某个作家,那并不是因为他把我们引入了一个至今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世界,而 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模样。在我迄今为止的阅读谱系中,这样的作家寥寥无几,博尔赫斯是最重要的一位。读这样作家的文章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有待填充意义的地带,而且它暗示出,一切含有形而上学意图的文学作品都像人生一样具有无限的可能性——这正是博尔赫斯意义上的“无限文学的化身”。 我从 来没有想过把写作当作一种职业,但却无时无刻不想把阅读作为终生的志业。到现在,我买的书越来越多,只能反衬出自己阅读的欲望越来越小,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。买书不是为了阅读,只是为了拥有它们,就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,仿佛在混乱的世界中拥有了某种神秘的秩序。
想起《别想摆脱书》中的那句印象很深的话:“我已永无可能在生活里获得平静,除非带着一本书远离人群。”这也许就是我无法停止阅读的原因:书是生活,书已经是生活,书已经是生活的所有。
文摘:书之爱,吾之爱
众所周知,卡夫卡曾经要求他的朋友马克斯·布洛德在他死后烧掉所有的作品,而布洛德最终违背了这一诺言,我们才得以认识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的天才。无数后人曾揣测卡夫卡烧掉自己作品的心理,各种说法,千奇百怪。其中最让我信服的是这样一种:卡夫卡之所以要烧掉自己的作品是一种自我贬抑的心态作祟,作家口中自称“一文不值”,而内心期盼的是无上的荣耀和夸赞“你身价非凡”。也许卡夫卡早就体会到,人们读一本书的唯一原因就是它们尚未完成,这让他们有发挥想象的空间。只有这样的书才配有永恒不朽的声誉,一如亚历山大图书馆付之一炬的珍贵藏书,因为这种残缺,在人们的想象中,书才更为尽善尽美。
之所以提及卡夫卡的故事,是因为想到了我们的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残缺的文学史,有数不尽的书遭受了各种摧残,再也寻觅不见。正因为如此,才催生了藏书家和书话系列的勃兴。我想有这种经验的绝对不只我一人:我们喜欢阅读一本小说,但是同类型的小说读多了让人厌倦;我们喜欢阅读一本书话,但是同样类型的书话,我们阅读时却乐此不彼。同样都是重复阅读,其中差别甚大。仔细想来,我们之所以喜欢书话,最重要的一点是,看似相同的搜寻好书的经历,在不同的人手中有着不同的韵味和惊喜。用阿尔维托·曼古埃尔在《阅读史》中的原话说:“事实的真相是,特别的书籍会赋予特别的读者某些特性。拥有一本书所隐含的意义就是,这本书先前的阅读史——也就是,每一个新读者都受到他所想象的这本书曾在前人手中的情形所影响。”书话看似重复一个搜寻好书的过程,但是每本书与每个人的相遇都是独一无二,他们的阅读体验自然也是独一无二。
我收集了很多书话系列,从内心而言可能是想搜集更多读书人的阅读和收藏的经验。浙江大学出版社旗下的北京启真馆策划出版了新的书话系列,命名为“书之爱”,此名可谓深得我心。最先出版的有美国藏书家爱德华·纽顿的藏书之爱系列三本,以及荷兰历史学家皮纳的《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》。纽顿的《藏书之爱》原来由重庆出版社出过合订本,我们并不陌生。书中介绍时说“少年纽顿于中辍学业后字商贩学徒起家,酷爱文学之余困知勉行”,又说他“平生最爱兰姆、狄更斯、布莱克、特罗洛普,哈代等英国大家,亦心仪约翰生博士、鲍斯威尔当代英伦文艺气氛”。纽顿是个约翰生迷,搜集各种版本的《约翰生传》,“硬纸简装、书口未裁的首版最受我钟爱,特别郑重收藏;同样是首版但附配插图的本子用来陈列;至于伯克贝克·希尔编辑的本子和我三十年前头一回读的廉价伯恩版,则专供翻查之用,因为我对那个本子可说是了如指掌”。当年就是因为你对这段话印象深刻,我才特意找来鲍斯威尔的《约翰生传》来读。书的记忆因此得以延伸。
博尔赫斯写过一首诗《一本书》,诗中最后一段说:“静寂的书架上,那静默的怒吼/沉睡在群书中的一册之内/它沉睡着,有所期待。”它期待什么?当然是有读者上前,翻开和阅读。书与其他工具的不同就在这里,人类制造的工具只是人手的延伸,只有书才是想象与记忆的扩大。书籍也许是我们借以了解过去的唯一凭借。所以一本书自然有所期待,期待后人去苦苦寻觅,在众里寻它千百度中,蓦然回首,灯火阑珊处发现它的存在,从而把历史与现代衔接了起来。
皮纳在《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》一书中就特意提到这种图书历史的困境,古代作家均不曾有完整的记录传诸后世,仅有只言片语,零星散落四方,通过口耳相承,得存片余,“如此以来,我们仅得一副拼图,由五花八门的残片连缀而成,却难言完整,不仅轮廓与细节无从判定,残片间的空白也让人头疼。”古人都不相信书本,觉得书籍这玩意保存东西太过于脆弱,而且一旦书写下来,思想顿时成形,无法继续传播。他们更乐意通过言传身教,口耳相传,在思想的传递中,也丰富了自身。所谓述而不作,是中西方哲人共同的选择方式。但是对我们现如今的人来说,仿佛只有搜集更多的藏书才能保存历史的记忆,我们恐惧的反而是电子时代的到来,思想记忆的传播和储存的手段变得更为脆弱。很简单的一个道理,一个500G电脑硬盘可以保存一个图书馆的电子藏书,这是它无以伦比的优势,但是如果一个传播的小病毒,一次硬盘的破损都可能导致一个图书馆的书丧失掉,这样的损失我们担负不起责任。我宁愿选择收藏实体书,通过一本本的搜集、收藏、记录、编写、整理,在不停的排列组合中,书写着自己图书的阅读史。
埃科的名著《玫瑰之名》是一本书的寓言,即是说,透过书的历史,我们可以重建文明的历史。书中自有教义,书不仅是容器,储藏所,更是“伟大的拐角”,从这个拐角出发我们可以观察一切,讲述一切,乃至决定一切。书是起点和终点。书是世界的戏剧,乃至世界的终结。我们通过收藏书收藏了记忆和历史,也复活了我们与过去的联系。每一本书话中我们都能清晰地探知到找寻书的历史。所谓“书之爱”,说白了其实是一种对自身记忆的追溯。我们的爱通过书这个媒介找寻到了过往生活的痕迹,颇为有点寻根问祖的味道。书话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自我探寻的心愿。
纽顿在《藏书之乐》中提到一手创建“龚古尔奖”的法国作家埃德蒙·德·龚古尔,说他去世前处理自己的藏书,特意注明了:“切莫移交博物馆冷藏,任由无心过客懵昧观览,务必托付卖场标售落槌”,只有如此,“余长年逐一搜罗各物过程所得之种种乐趣滋味、品味雅兴,方可再度一一施与同好中人矣”。琢磨这些话很有意思,藏书的过程最快乐的部分不是你占有了某本书,而是孜孜以求,苦苦寻觅的过程。如果你不能体会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咸,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心得体会,更不会在意这本书对其重要性。捐给图书馆的藏书大都湮没无闻了,因为再也没有重新发现的快乐可以描述。只有通过不断的流通,我们方能察觉一本书在经不同人之手后留有的一丝微妙的痕迹。比如说,我们知道曾经有谁收藏了这本书,为什么他又卖掉这本书,这本书在流通中发生了什么故事。这才是活生生的书话啊。
你拥有一本真正的藏书,这是你长期努力建构的杰作,这份藏书显示了你的天性,就如同你为人的性格,为文的风格,是你独特的“灵韵”。如果你的藏书某一天被整齐划一地捐给图书馆,进入那个毫无生命声息的上架行列,这份藏书再也与你无关,它的生命只能在被动等待人翻阅的时候,才可能有些许的生命苟延残喘。但是如果重新进入流通市场,一本本书仿佛入水的鱼儿,在畅游海底的世界中,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等待我们书写。
我为什么喜欢书话呢?想来想去,也许是因为书话带给我们一种幻想,读书人不孤独的幻想。在搜寻一本本图书的过程中,我们发现了共同的快乐和神奇,我们也深知这样的探寻无穷无尽,也许是无底洞的深渊,也许是梦幻的天堂,但是如果我们能从中找寻到读书人共同的快乐,知道吾道不孤,这也就足够了吧。
来源:金城出版社


